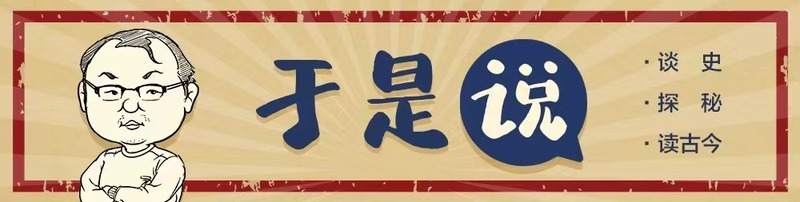
在南京生活,常常能听到关于野猪的新闻,甚至很多人还亲眼目击过野猪,早已怪不怪。但最近的“野猪”新闻还是全城皆知。一头野猪这次玩出了“新高度”,接连闯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和江苏电视台。要知道,前几年就有野猪冲入了地处郊区的南大仙林校区,没想到此番又有野猪“打卡”了位于南京市中心的鼓楼校区。

很多人对家猪很熟悉,对野猪则感到陌生。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把野猪驯养为家猪。猪因而成为六畜之一(马、牛、羊、猪、狗、鸡)。它不但是古代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更是生活富足、丰衣足食的代名词。在江苏的博物馆里,同样能找到很多和野猪、家猪相关的文物,体现着古人对猪的崇尚和喜爱。

最早出现野猪形象的器物,可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一件1977年出土于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猪纹黑陶钵。陶钵外壁和内壁上,河姆渡先民用高度写实的手法,各刻绘了一只长嘴大耳,头向前垂,双目圆睁,正在寻觅食物的野猪。这件陶钵是实用器,将如此造型逼真的野猪图案绘在日用器具上,说明河姆渡先民对这种动物很是熟悉,也有几分喜爱,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了对野猪的驯化和饲养。

此外,河姆渡还出土过一件陶猪,造型同样类似于野猪,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方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一种被称为“玉猪龙”的玉器也常被发现,它们是早期猪和龙的结合体,头部似猪、身躯如龙,充满着神秘色彩;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过一件“红陶兽形壶”,是一只昂首挺胸、憨态可掬的小猪,距今6500—4500年,被列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新石器时代的猪形陶罐是南京博物院的“明星展品”,长期在历史馆展出。它们大小不一,造型各异。陶罐就是小猪造型,口部开在猪背上,很是实用。这组猪形陶罐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5000年。在龙虬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先民吃剩下的猪骨骼,经鉴定,大部分个体年龄为1—2岁。龙虬庄发现的猪形陶罐,体态丰腴,体形浑圆,吻部短小,四肢粗短,显然是家猪。结合考古材料分析,龙虬庄发现的猪骨骼也属于家猪。当然,龙虬庄先民驯养的猪,其“祖先”当然是来自生活在野外的野猪。和野猪相比,这些家猪的耳朵变大,耷拉下来,脸部变得浑圆,吻部变短,獠牙缩小,这些当然是野猪被人类驯化后发生的改变。它们不再需要竖立的耳朵、突出的吻部、尖利的獠牙来侦察、发现和捕捉猎物,但也因此迎来了被人类圈养、成为肉食的命运。


当然,南博的这几件猪形陶罐是极为可爱的,它们生动逼真,小的如同茶盅,大的如同零钱罐,有的翘嘴睁眼,有的抿嘴拱鼻,有的眯眼憨笑。设计师们从中获得灵感,他们以小猪陶罐为原型,设计出冰箱贴、毛绒玩具等文创产品,成为南博极受欢迎的“文创爆款”之一。

以野猪为形象的史前文物,在常州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件,这就是2002年出土于常州新岗遗址39号墓的猪形陶尊。新岗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且序列完整的崧泽文化遗址。崧泽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龙虬庄文化则分布在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平原。两处遗址都出现了和猪有关的文物,证明史前时代,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北,野猪广泛分布,先民们都已开始对猪进行驯化和家养。

春秋战国以后,文物中的“猪”绝大多数是家猪的形象。这样的文物很多,大部分是墓葬陪葬品。因为肥硕的家猪也是财富乃至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古人常常用和猪有关的明器陪葬。比如,死者握在手中的“滑石猪”,就寄托着逝者希望将财富带去另一个世界的愿望。“滑石”是一种矿物,质地柔软、滑腻,容易雕刻。用滑石雕刻成明器,又是猪的形象,还握在死者手中,我们不妨称之为“掌上明猪”。

陶制猪圈是从汉代到六朝时期常见的陪葬品,反映的是死者生前的庄园经济生活方式。到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些青瓷猪圈明器。有的猪圈连着厕所,汉代人称猪圈为“圂”,称带厕所的猪圈为“溷”。“豕”就是猪,“圂”“溷”这两个字非常形象。我们这里提到的滑石猪、陶猪圈、青瓷猪圈在南京博物院、六朝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等馆内都能看到。

此外,从汉代到南北朝的一些画像砖上,也能看到古人养猪、杀猪烹煮的画面,这种画像砖在江苏就很少见了,在四川、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相对较多。
现代人看到野猪,大呼小叫,赶快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但古代江苏人看到野猪应该是见怪不怪的,这反映在文学里,和江苏人有关的几部文学名著其实都写到了野猪。
淮安人吴承恩《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其“原形”就更像是野猪,书中描写猪八戒“碓嘴初长三尺零,獠牙觜出赛银钉。一双圆眼光如电,两耳扇风呼呼声。脑后鬃长排铁箭,浑身皮糙癞还青。手中使件蹊跷物,九齿钉耙个个惊”。碓嘴、獠牙、脑后有鬃毛,活脱脱一副凶猛的野猪形象。《红楼梦》里也有“野猪”。第五十三回写道,庄头乌进孝给宁国府送年货,账目上就有“暹猪二十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暹猪”应该是从暹罗国(泰国)进口来的猪,“龙猪”是产自南方的一种小猪。野猪和暹猪、龙猪都是宁国府贾家餐桌上的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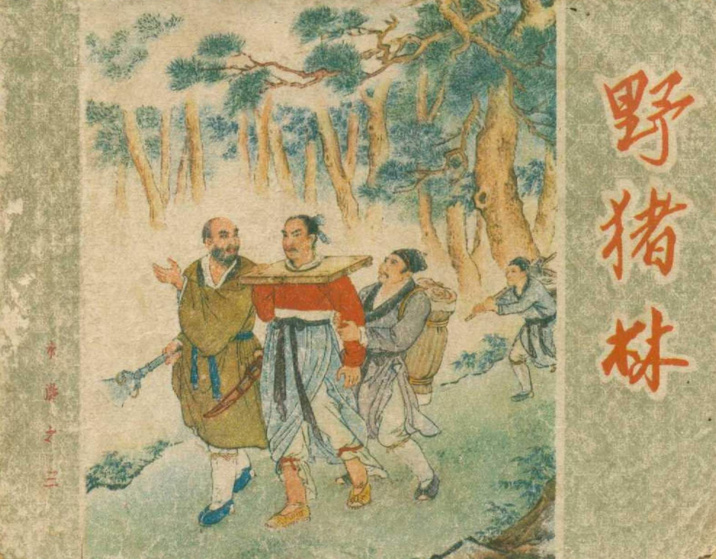
施耐庵的《水浒传》里有一个重要的地名“野猪林”,就是董超薛霸要谋害林冲的地方,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说,“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可见在那个年代,野猪出没的地方,往往是位置偏僻、环境险恶,过路行人要多加小心。由江苏人整理创作的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商纣王阵营的“梅山七怪”中,就有一个野猪精朱子真,凶狠残忍,现出野猪原形,咬死周将余忠,并一口将杨戬吞入腹中,但最后还是被杨戬用计所杀。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