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步才
我妈杨胡氏走了,享年虚岁91。
那天是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七。我侄女说:奶奶真会挑日子,选在七夕情人节,去和爹爹相会了。
侄女口中的“爹爹”,就是我父亲。在我老家,小时候我们喊父亲叫“大大”,喊爷爷叫“爹爹”。大人喊小孩,一律叫“伢子”。我13岁那年,刚进初中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病故,母亲37岁守寡,拉扯着我们4个兄弟姊妹,艰难度日。

我读初中的那3年,正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3年间,每当庄稼收获季节,不见天日的连阴雨就接踵而至。麦子尚未脱粒,出芽了;玉米还立在地里,长毛了;山芋、花生来不及刨,霉烂了。年复一年,年年如此,你种什么,老天让你失收什么。饿得百姓把能充饥的水草捞光了、能下咽的树皮剐光了,撑不住的乡亲浮肿丢命,活下来的乡亲一脸菜色。我大伯见我家母子的日子实在苦,就逼我母亲让我辍学。他说:“大伢子就是在家割青草,一年下来也能晒上两个干草堆,不比读书强?”我妈没答应。家里实在没什么吃的东西能让我带到学校去了,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胡萝卜,从地窖里挖出来,洗净了、剁碎了、晒干了、炒熟了,再磨成“炒面”,装进一个手帕缝成的小布袋,背着弟弟妹妹塞给我说:“乖乖,晚自习后抿两口,压压饥。”初中3年,我做得最多的美梦,就是山芋藤变成了面条,篮球变成了大肉圆。初中毕业时,班主任施老师劝我弃考高中。她说:“你妈妈太不易了,考上淮中也上不起。考淮安师范吧,师范生书本费、吃饭钱都不用自己掏。”

淮安师范是师资一流的省立名校,因“三年困难时期”已停招数年。我们1963年考进去的“66届”,在5个县只招两个班80人。我进校以后,那些三年级、四年级的学长们还在校等分配。这时,国民经济虽已起步“调整”,但仍物资匮乏,淮师学生的伙食是免费的“两稀一干”,早、晚餐每人3铜勺稀粥,中午每人一瓦钵大麦采子干饭,每周还必须吃一顿雪菜炒肉丝之类的小荤。对我而言,那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的幸福。更让我珍惜的,是每周六中午固定供应一顿馒头,白面的,每人半斤。这一天的白面馒头,我很少舍得吃,多数是留下来星期天徒步赶回家,去喂我老妹。在我父亲去世时,老妹还在妈妈腹中。每当看到她四五岁了还骨瘦如柴,当大哥的我就想哭。省下的那块馒头,可以让她泡开水吃好几顿。
师范毕业了,我进了一家报社,家境一天天好起来,母亲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父亲去世以后的岁月里,她白天要挣生产队的工分,收工后要摸黑侍弄家里的自留田。寒暑假回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看到她就着火苗如豆的油灯,在为我们几个孩子缝袜补鞋。日子一天天艰涩地流淌,妈妈的腰越来越弯,背越来越驼。再后来,时不时地发作哮喘,厉害时整宿不能平卧。73岁那一年,她吓过我一回,镇医院的医生说她不行了,我连夜赶回去,把她转入地区医院治疗。84岁那一年,她又让我虚惊一场,已经要为她穿寿衣了,她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又过了六七年,这次老人家竟然毫无征兆地走了。妈妈临走那天凌晨,我在南京的家里睡梦中被冰凉的水滴惊醒。一向无故障的壁挂空调突然从风口处往下滴水,溅我一脸。我拿来接水的盆,水又不滴了。我再次躺下,不一会老家的电话来了:“大哥快回来,老人家不行了。”
我母亲的丧事是在市郊的租住房办的。老宅连同左邻右舍几个村的民房,半年前就被推土机推平。据说征地是要建生态新城。按习俗,有个环节叫送饭。老辈人指点说,还是要送到老宅那边去,送在当地她拿不到,也吃不上。从牧皋大桥迂回到老宅原址,供上饭菜、烧纸上香。妹妹悲痛地呼唤着:“妈妈,饭来了,三顿并一顿送来的,往后你就自理了。”透过香火烟雾,我看到老宅四周,从东到西是荒草、瓦砾,从南往北,还是荒草、瓦砾,“生态新城”还只是传说。我坚信,蓝图定能成现实。但我又担心,待到日后,面对连片的高楼、新城,妈妈,你还能找到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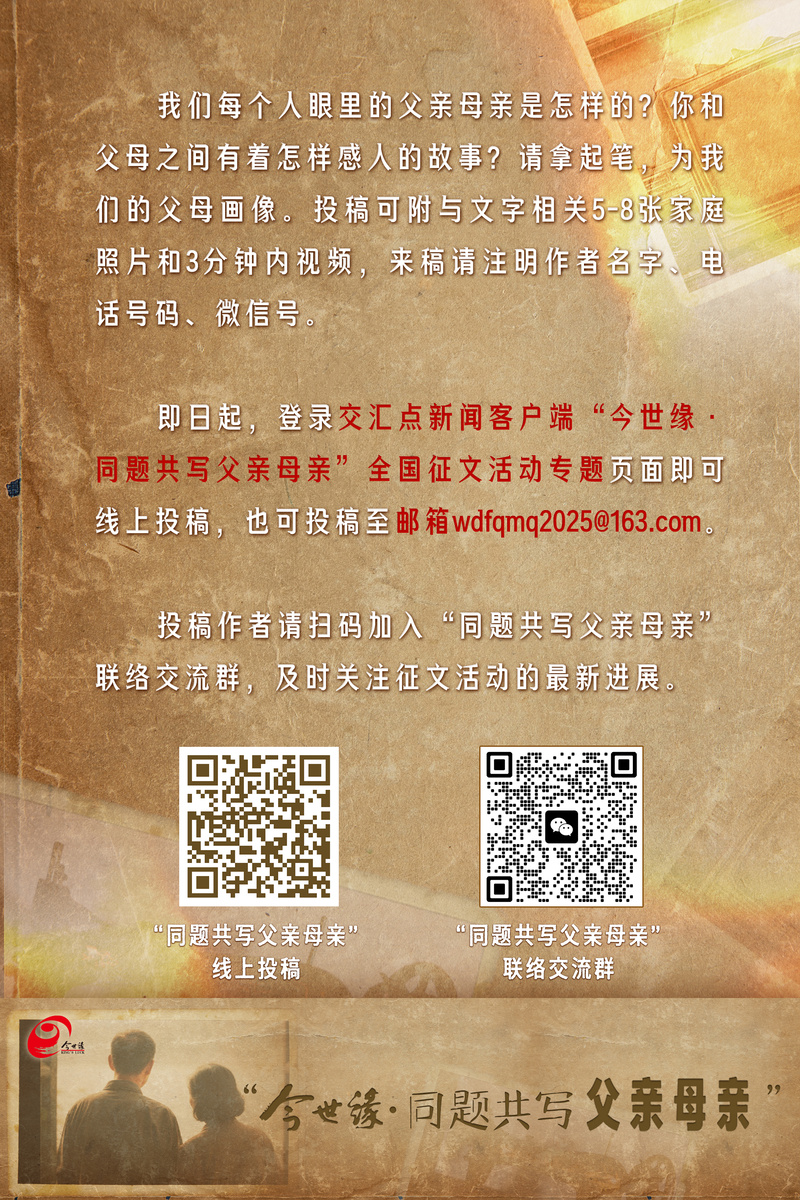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