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自古以来源远流长、根基深厚,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诸多能工巧匠,精品迭出。进入新时代,长三角地区民间手工艺凭借深厚文化底蕴与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发展水平依旧保持在全国前列。纵观各个工艺领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善以传统师徒制为基础培养传承人,保证了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美学风范的代代传承。
一、“工巧”:技艺的师徒传承
《考工记》提出,好的工艺必须“材有美,工有巧”。数千年来,从事工艺行业的能工巧匠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工巧”,探索“工巧”的秘诀。从古至今,长三角地区始终是能工巧匠的聚集地,不断以杰出作品诠释着“工巧”美学。7月25日下午,“匠心独运 山花绽放”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师徒作品邀请展在苏州市文联文艺家展厅开展。从本届邀请展来看,参邀作品丰富多彩,涉及刺绣、石雕、木雕、瓷器、剪纸、紫砂、盘扣、漆器等多个类别,都有着“工巧”的共同美学特点,既巧思倍出,又精工细作,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师徒共展,更让人直观感受到了“工巧”美学的代际传承,既呈现了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的美学高度,也展现了新时代年轻传承人的巧慧与匠心。此间,新时代的师徒传承方式尤为值得注意,正依赖于此才将那些难以言说的默会知识在身体场域中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工巧”美学乃师徒之间需要传承的默会知识,师徒传承的目的正在于传递不易被知识化的“巧”技。
所谓“工巧”,并非仅仅是指对材料的巧妙处理,尤为重要的是“巧妙”之中不仅要有新思与技艺的创新,又要始终立足于传统技艺。究其根本,民间工艺虽有着技艺革新与超越的内在要求,但本质上是为了“精益求精”,而非为了表现个性刻意“求新求异”。所以传统民间工艺并不追求大刀阔斧的技艺猛进,而是在点滴精进中提升技艺,在传承中稳步发展。自古以来,对“巧”的思想阐述都在证明“巧”并不是简单的事,更不是浮于表面的奇观。例如,道家认为“大巧若拙”,讲究去机心重偶然、去机巧重天然、去机锋重淡然,反对华而不实、过度雕饰,这是一种道之“拙”,是对自然本真的追求。故而,“巧”的最高境界反而是以“拙”的面貌呈现的,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就是推崇一种看似不经意修饰的、自然天成的韵味美感;儒家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强调工巧也要守住“善”的底线,“巧”与心性修养密切相联。可见,在传统美学思想中,“巧”是以求真、求善为底色的。受到东方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民艺家柳宗悦格外推崇工艺的健康美,认为工艺应朴实无华、符合人性。
以“工巧”美学观之,本届师徒邀请展所展出的作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善于处理传统传承与技艺创新之关系,既呈现出坚守传统的匠心,又能在此基础上呼应当代审美需求;二是善于处理材料,讲究技法浑然天成,凸显点滴意趣,有其内在的真、善、美。即便雕刻类的作品,虽细节繁复,却也无堆砌之感,充分呈现出“以简驭繁”的特色。同时,从这些各具特色的工艺作品中,也能让人在技法之下体会到自然流露的生命态度。例如,蒋喜师徒的玉雕作品《缘弧饰玉》充分展现出“化朽为奇”的高超技艺,对玉器边角余料作了一次精妙的艺术呈现。其结合现代人的简约审美,既充分发挥了余料原有的弧度之美,又将古代玉雕中美好的点、线、面尽情融入作品之中,展现了传统玉雕的祥瑞神韵,可谓简约却不简单,意蕴丰富,实现了传统技艺、巧思与现代审美的精巧融合。又如,程礼辉师徒砚雕(歙砚)作品《春江水暖》颇具匠心,特色显著,一是利用砚石上天然的白色石英来表现春山残雪之景,二是借用砚石上的罗纹纹饰呈现微波春江之水,在尊重砚石自然肌理与纹路的基础上发挥创意。整个作品构图充分体现“石因工美、工因石巧”的艺术理念,将自然之美与工艺之巧相融,几株枯树、三两村舍、临水溪桥,意境全出,苏轼诗句“春寒料峭雪初消,村郭野径临溪桥。鸭试新波知水暖,东风犹在杏花梢”的气氛跃然石上。诸如此类巧夺天工之作,在本展览上俯拾皆是,尽显长三角民间工艺的工巧水平与审美格调。

上述共同的美学特点显然与师徒相传有关。技艺本质上是一种无法口传的隐性知识,只能依赖于身体之间的交流与默会,而这种隐性知识往往是使得工艺达到“巧”之境界的关键。波兰尼指出,“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存在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难以正规化、难以沟通的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关键部分。隐性知识主要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和感知,源于经验”。一般来说,能工巧匠在长期的技艺训练中所形成的通常是一种高强度依赖于身体的经验,这种具身性的经验充满着个体化的体验、志趣与品味,交织着微妙的技巧、秘诀、感受与心理,这也是民间工艺传承中最难以传承的部分。各类民间工艺中所谓的“诀窍”,基本都是对特殊身体经验的总结。比如,刺绣中的针法、陶瓷烧造的火候、锻造工艺中的力度把握等,这些技艺的精熟掌握表现在对身体感觉的体会与特殊经验的领悟,都只能身教而无法言传。我们说工艺的“巧”或“拙”,其实也是在评判手艺人身体的熟练性或灵敏性。相较于正规教育,师徒制无疑是更符合隐性知识传承的方式,师傅更能在不断示范中传递这些身体性的、默会性的知识。从本届师徒作品展览中可以看出,工艺的隐性知识在年轻一代身上传递着,不然难以呈现出技艺的精湛与调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例证了师徒传承制在长三角地区民间手工艺传承与发展模式中的必要性、有效性。
二、“精雅”:审美旨趣的师徒传承
如果说“工巧”是师徒传承的技艺根基,那么“精雅”则是师徒传承的审美取向,前者是技艺精益求精的薪火相传,后者是审美观念的代际相承。所谓“雅”,可以是雅致、文雅,也可以是古雅、文雅,既表现为视觉上的典雅韵味,又呈现为内涵上的品味格调。这种“精雅”的审美观念在本届师徒邀请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表现于陶瓷、竹刻、紫砂壶、香炉、鸟笼、刺绣、石雕、木雕等各个工艺门类。虽然工艺大师们的作品形态迥异、各具特色,但基本来说都是有着“雅化”的内在追求,有意无意展露出“精雅”的审美取向。按理说,民间工艺是在广阔的民间环境孕育出来的,应以地方乡土美学为特色,其本身应与学院派、宫廷派有所区别,一定程度上会与“雅”文化泾渭分明。但实际上,“雅化”始终是长三角地区工艺品的重要特点,这种“雅化”的取向不仅当今有之,而且古亦有之。在历史上,民间工艺的雅化现象滥觞于宋代,极盛于晚明。晚明文人张岱专门点评过民间工艺界的翘楚,“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许多文人评价民间工艺时,常用的词汇也是“雅”“古”或“古雅”。如褚德彝品评濮仲谦的浮雕竹笔筒“浑古朴雅,灭尽斧凿痕”。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的“精雅”美学传统与该地区历史上文人荟萃密切相关。文人出于文房清玩、书画装裱、书斋布置、园林营造等日常需求会挑选一些符合自身审美观念的工艺品,由此造就了民间工艺品的文人消费市场。而且,长三角地区历史上文人与工匠的交往一直颇为密切,文人审美观念难免影响着匠人群体,许多名流千古的能工巧匠都有着自觉“雅化”的意识与追求,不仅认同文人的审美趣味,还努力精进技艺、提升审美眼光,使得民间工艺不再拘泥于技术,而是能由技及道,拥有一种形而上的审美精神。事实上,恰是较为成熟的文人消费市场的支撑,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的雅化才有了强大的拉动力量,才成为“雅化”的代表性区域,并呈现出不逊色于精英艺术的美学格调与文化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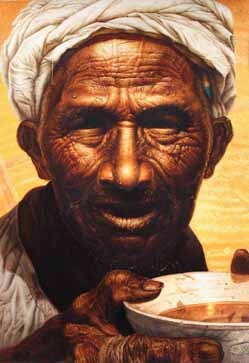
从本届展览来看,当代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审美取向主要还是秉持传统的“精雅”审美旨趣,充满着古典意趣。即使是新生代传承人的作品,也颇为重视与强调“精雅”“古雅”。这种“雅化”审美取向在很多作品中都有亮眼表现,比如葛志文的石雕作品将自然纹理与文人意趣融合,善于营造“枯雅”意境,具有妙造自然的艺术特点;姚建萍以针为笔尽显苏绣的画绣特色,其雅化理念进一步被姚卓所秉承,且更具有时代性;钱月芳的顾绣作品《牧牛图》绣出写意画的干湿浓淡和笔触墨韵,虚虚实实,显现画的意境和神韵;陈传发、张国豪的南派鸟笼结合了竹的坚韧与玉的细腻,风格古典雅致,凸显自然和谐之美。传统的“精雅”美学之所以源远流长,并能在当代社会传承发展,究其原因,一是民间工艺的特质不仅在创新,还在于其“传统性”;二是民间工艺消费群体的审美观念有着较好的历史延续性,当代审美风尚也乐于接纳古典主义趣味;三是民间工艺在当代社会的实用价值日益削弱,需要以审美价值为中心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发扬传统审美特色使之蜕变为艺术品。
当然,当代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传承“精雅”美学,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固守传统文人审美意趣,而是在传统传承中不断再发展与再创造。在本届展览中,有些作品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雅化”路径,展现出新的时代气象。例如金文、庞琬婧师徒二人的《如云显威》《如意之旋》都打破了传统的云锦图案,剥离了写实的云锦语言,转而使用抽象的艺术语言为云锦注入了新的活力。庞琬婧《如意之旋》以传统文化中的如意图案为基础,通过如意之旋的图案结构展现当今社会的“卷”,颇具有时代气息。李守白海派剪纸《百年上海》融合东西方美学,将西方抽象、装饰等手法引入剪纸,丰富并提升了剪纸的艺术表现力。可以看出,传统审美精神具有再生产的潜力,越来越多的传承人开始以当代眼光重新打量审视传统工艺题材、图案、色彩,不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兼具传统特色与时代意蕴,此乃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审美“雅化”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三、美学精神的传承: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师徒传承的意义
长三角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民间工艺的富矿地,孕育出诸多世界级非遗工艺,这些工艺的延续离不开师徒传承的优良传统。对于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的发展而言,师徒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美学精神的活态延续。正是对“美”的极致执着,塑造了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的非同一般的审美品格,确保其数千年来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实现了“工匠精神”与“美学追求”的深度融合发展。
一般来说,师徒传承的核心恰是在于将“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工艺美学理念以身体为中介,以具象的技艺实践传递给后学者。如果缺乏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就难以深入把握凝聚在工艺之中的“匠心”与美学品格。所谓“匠心”,其实不止包括对技艺的精湛追求,也包括对审美的追求,并且最终都要以形态美、内涵美的工艺精品呈现出来。对于很多新手而言,除了日复一日的技艺训练,以达到技艺的娴熟,更难的在于培养审美眼光,从而深入理解凝聚在作品之中的美学精神。无论哪一样,都离不开身体训练的耐心、守拙的功夫,同时更要在技艺磨炼中体会“一针一线的诗意”“一刀一凿的哲思”。一定程度而言,只有跟着师傅,朝夕相处,耐心学艺,才能获得学校教育无法教授的隐性知识,慢慢锻炼出审美眼光,领悟审美精神。而且,师傅长年的技艺坚守精神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徒弟,给予其持久的鼓舞,支撑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传统手工艺师徒传承的意义本质上在于实现美学精神的活态传承,将“无形”的审美趣味、记忆、情感、品格、信仰等在点滴日常中传递下去。
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主要根植于江南地域文化语境,具有雅致温婉、虚实相生、雅俗共赏等特点,本质上是工匠对江南地区自然、生活与文化深入观察并融会贯通予以艺术化表现的结果。这种美学精神继承了文人艺术的意境美学,又着重突显出富有诗意的生活美学。这种美学精神是在师徒传承中不断衍生发展的,不过,师徒传承并非仅仅强调对传统美学的继承,而是鼓励新一代传承人在深刻参透美学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响应时代审美需求的创新转化,努力赋予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美学以新的生命活力。事实上,我们在本届许多展览作品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转化,活态传承美学精神,使之具有时代性,更加富有当代气息。这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际上秉持了传承与创新的辨证准则——工艺语言与表现形式可以变,对意境、韵味的追求,对工艺材料的尊重、对工艺细节的执着不变,从而通过不同代际的美学对话与传承,真正实现了长三角地区民间工艺美学精神在当代创新性表达。
作者:季中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