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讯 陈彦堂(1917.10-1993.2),字子升,盐城伍佑人,原籍盐城南洋镇。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历任乡长、校长、教导主任、工会主席、区教育辅导员、代文卫助理等职。抗战时负伤,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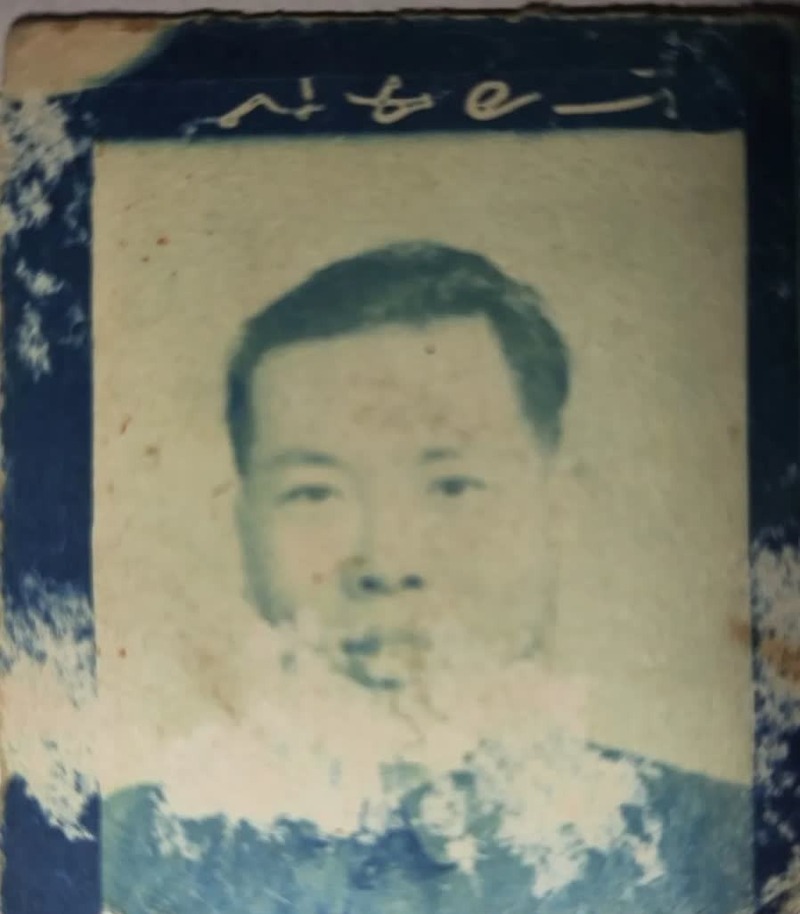
1924年2月,他就读于盐城南洋湘陵、强武、俊卿等私塾,他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八年刻苦,通读了《四书》《五经》及唐诗、七家诗等古典书籍,学会裁诗撰联,书写楷、草、行、隶、篆等字体,尤为楷、隶甚好。1935年1月,弱冠年华即设馆教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知识青年成为各方争抢的对象。1939年,他正在家乡教学时,很快被在盐城做地下工作的李寄农同志发现,并一心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他很快划清了敌我界限,成为骨干分子,受到重点培养。
1940年10月,盐城首次解放,中共民主政权初建,李寄农任盐城民主政府首任秘书。11月,在盐城各乡召开选举会议中,他经民众推选,县政府委任,担任盐城县二区正年乡乡长,李绍林任乡长助理(后牺牲,盐城烈士命名村之一——绍林村)。任职后,在抗日斗争中,政治立场十分坚定。
1940年11月,在陈毅、刘少奇的直接关心下,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创建。李寄农安排他到五分校接受教育,成为首期学员,经常聆听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等作的抗日动员报告,思想上深受启迪,政治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爱国热情不断加深。期间,在党的关怀下,他正式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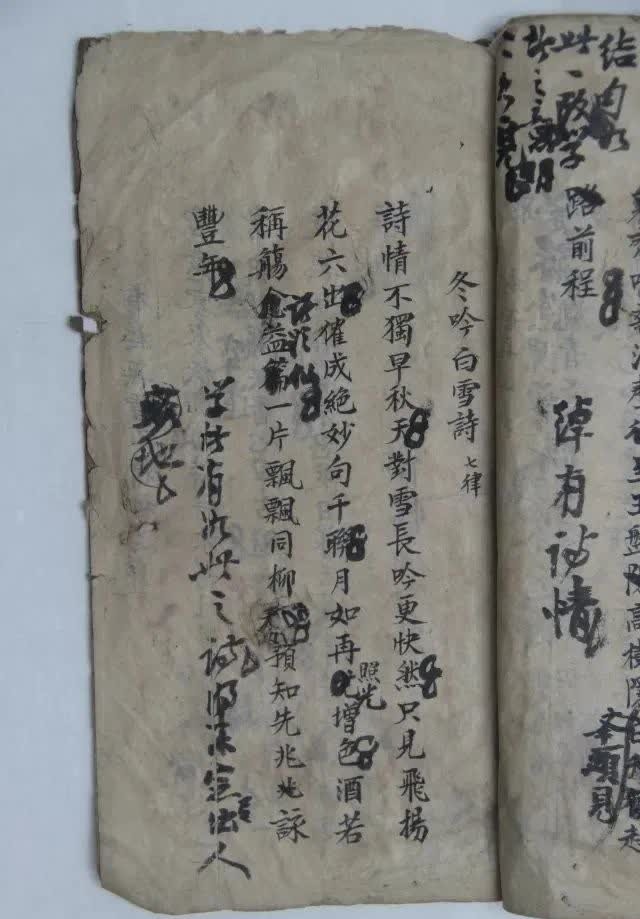
日寇入侵盐城后,形势十分险恶,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据南洋的陈汉回忆:为了便于抗日,共产党采取化整为零的政策,将盐城划分成若干根据地。起初,南洋先成立了东乡办事处,时间不长就建立了南洋区,不久便成立了盐东县,后又改为南洋区。时任区委书记许庄,区长何萍。区政府一天夜里能迁几次是常有的事。
“乡长在哪,快把人交出来!”80年代初,我记事时就常听奶奶回忆道:那时“和泥军”(即日伪军)在扫荡中,到处打听爷爷的下落,全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41 年秋,由于找不到爷爷,敌人气急败坏地一把火把将爷爷家住房全部焚毁,可惜入党材料也一同焚毁。爷爷曾留七言律诗《血洒疆场志不倾》,于1989年4月在《离休老干部诗词选》发表,诗言:抗日于今已五旬,回忆往事记犹新。硝烟遍地弥华夏,炮火连天泣鬼神。承党授权乡政建,拒倭反伪住房焚。虽遭巨损毫无惧,血洒疆场志不倾。充分表达了他在风刀霜剑的年代,将生命置之度外,积极发动民众奋起抗日,坚持反伪化、反“扫荡”的武装斗争,全身心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日事业当中。
国仇家恨,更加深了爷爷对日寇侵略华夏、屠杀同胞的仇恨之心,坚定了原地斗争的决心。1942年1月,在日寇一次下乡扫荡斗争中,爷爷不幸被俘。在押往敌部的路上,爷爷宁死不屈,遭日寇开枪倒地,日寇又用枪托击打其头部数下。此时,鬼子的集合哨吹响,见满地鲜血,以为人已打死,便丢弃在路旁的草丛中。
所幸,在敌人走后不久,幸被附近群众及时发现,经确认,正是乡长陈子升,遂迅速将倒在血泊中的爷爷抬至后方医院进行救治。经查,枪弹偏中于右臂,将臂骨部分击碎。后经医生数次手术,取出碎骨三十余块。因当时医疗条件差,水平有限,直至1943年底碎骨拔清才基本愈合。1942年秋,在二条港养伤期间,爷爷曾写下鸣谢二条港孟曼华、孟新生娣弟对联一副:“同胞同业,同救举世,同胞遐迩感同恩,不独元龙同再造。妙手妙方,妙用回春,妙手中西驰妙誉,咸称扁鹊妙重生。”亲笔手稿至今还珍藏着。
爷爷身残志坚,在负伤期间,仍不忘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在爷爷七十寿辰时,学生史安民、余尚进等为他所写《寿序》中提到:“为治伤求医曾来三龙镇西,与吾师、吾友及那时旧友,谈诗论文,胸怀磊落,遂与之设馆于‘三愧’,诸生喜集门庭,感受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后因三龙镇为敌窃踞,又驾返故乡。”1944年,伤愈后,由于爷爷身体虚弱,不能继续参加游击性斗争,经区文委安排,他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协助抗日,继续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在解放战争中,他仍坚持一边教学,一边协助地方征运公粮,支援前方作战,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经常下乡扫荡,教学很不正常,敌人枪一响,爷爷就带着学生躲藏起来,把课本藏在田埂边早已挖好的洞里,在田埂边教学是常有的事。在斗争中,他还经常写墙头诗,利用夜幕掩护,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捷报。在大团、便仓、伍佑等盐南战斗,以及渡江战役中,他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积极运送公粮到前方一线,曾多次立功受奖。二伯在纪念爷爷去世十五周年时曾写有《送军粮的故事》一文,详细描述了在1947年冬月,盐南阻击战即将打响前,二伯与爷爷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为解放军战士送军粮的故事。
在抗战中,区文委李绍林、乡农会会长余兆荣……都成为了烈士。爷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幸免于难,比起他们确是幸运的。“烈士生前是苦根,自从土改获翻身。主持农会尊民意,执政乡闾感党恩。可恨倭奴凶兽性,堪嗔顽匪野狼心。虽然肝脑遭涂地,留得英名万古馨。”1991年7月,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时,爷爷心潮澎湃写下一首《追思余兆荣烈士》的七律诗,表达他内心的深切怀念。
呕心培桃李,沥血育新苗。新中国成立后,他忠诚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自区文委安排从事教育工作后,他主要在余湾、舍北、双福、中舍、同福、合兴、民主、南洋、南陵、东坍、陈家等校工作二十余年。常备课教学以忘食,批阅作业以废寝,尽心竭力,为国育才。真乃盈门桃李峥嵘,一代良师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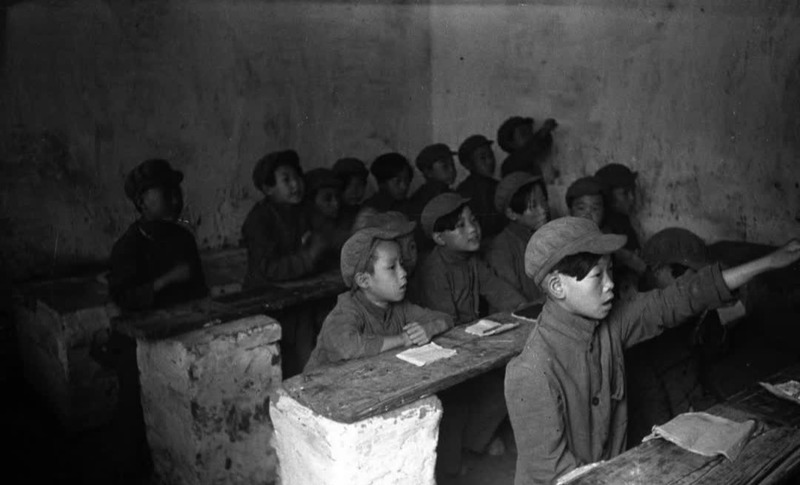
50年代初,他曾当选乡、区人大代表,县、区先进教育工作者。一九五六年,他与蔡长青同志被选送到南京教育行政干部学校脱产学习。一九六二年,县民政局局长张万松同志知道他抗战负伤,亲自登门动员他体检复查,补评为二等乙级残废。直至六六年,因伤残复发,身体虚弱,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老迈豪情赋雅兴,享受晚年桑榆乐”。爷爷一生,谦虚谨悫,勤奋好学。诗词曲赋,潜心钻研,尤为诗词,妙笔传神。然爷爷从不自满,古稀之年,应昔日挚友相邀,同进市老年大学,续学四年有余。与宋金城、唐栋、吴少棠、杨庆增等同志谈诗论文,唱和诗篇,先后成为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其间,他不畏路遥,不惧寒暑,吟诗挥毫,笔耕不辍,遗诗万言,流芳千古。
尤为令人感叹之为爷爷已身患重病,日渐黄昏,仍壮心不已,坚持学完规定之课程,直至时任老年大学校长徐植将毕业证书和优秀学员证书送至病床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然此好学上进之精神,焉不令人可歌可泣者乎!短短四年,他共写下一百六十多首优秀诗篇,大多选登在《校园诗草》、湖海文艺社、老年大学报及国家级诗刊上,著有《陈子升诗文集》。他的诗朴实、精深、工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对新生活的无比热爱,对同志、战友的深情厚谊,对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热烈拥护,体现了一位民主爱国人士(党员信息丢失)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1992年春节期间,爷爷因中风就医。直至1993年2月病逝。回忆爷爷的一生,他光明磊落,赤胆忠心。深受众人敬佩。在生病住院期间,有关领导与战友到医院探望慰问。他仙逝时,政府及工作过的单位、好友都书赠了挽联、挽诗词,摘部分如下:
学生苏颐:
诗文并茂古镇含悲悼艺苑奇葩,
桃李天下新潮涌浪奠教坛元老。
学友徐展:
为抗战立功为社会立德为吾侪立言为家庭立业诚为人间留正气,
有荣华不羡有高位不贪有功劳不炫有声望不居自有楷模亮节风。
学友马东:
反伪化建政权德冠故里民尽仰
培桃李育英才望重杏坛众皆钦
大丰三龙镇离休干部 后学孙志群:
初建苏区任职时,领民抗日展雄姿。
飞来子弹穿肱过,幸遇我军妙计施。
自费寻医伤口治,忠心爱党志不移。
功劳浩瀚垂青史,盛德永为后代师。
以上诗词无不充分表达了他是一位为国为民、廉洁奉公、助人为乐、谦虚谨慎、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一代良师”。(陈卫江)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