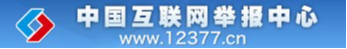文丨张大勇
还没等摄影师的“茄子”落下,也未来得及摆出笑容,人群里已经漾开了一片笑声——一次,两次,许多次。第十次江苏省作代会上,摄影师的快门未响,笑意已盈盈。
正午,南京国际青年会议酒店五楼内的光线明澈温润,代表们佩戴的红色胸牌,在光华中泛着暖泽。人们依照引导依次入座、站立,如层层舒展的花瓣,围成一个饱满而庄重的整体。摄影师与助手细致地调整着每一处细节,从衣襟到姿态,从神情到间距,从个体的形象展示与整体的美学构成,正待按下快门时,又有几位匆匆赶来,胸前的红牌随步履轻晃。如此反复,场上的笑声便也一波接着一波,是谅解,是欢愉,也是等待里生出的暖意。直到数声清脆的“咔嚓”响起,伴随着几下扎实的快门声——庄重而圆润,像一粒石子投入玄武湖,漾开了一圈圆满的涟漪。
我来自基层,来自文学“县”场,首次参加这样的盛会。会场内外,见得最多的便是合影。老友重逢要合影,新识初遇要合影,不同群体、不同场合,镜头前的人们总含着笑意。如今早已是影像自由的时代,不止相机,手机也时时闪烁。盛事难得,名家汇聚,领导讲话带来的群情振奋,“合影”成了这段冬日时光里最鲜亮的一笔,是纪念,亦是表达。
我自然被这样的气氛感染,起初只是腼腆地与会场景观合影,比如过道的标识、大剧院门前滚动的荧幕、会场里庄严的横幅。后来,胆子便大了一些,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望:想与景仰已久的作家合影。

机会来得恰好。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前,场外那面喜庆的红色背景墙前,毕飞宇主席正被一波波上前合影的人环绕,环绕。他始终含笑而伫,风度温和。我瞅准一个空隙快步上前,轻声报上身份:“我是盐城阜宁的。”他“噢”了一声,嗓音清亮而厚实。我喜欢听他讲话,字字清晰,既有思想的重量,又散发着一种生动的气韵。就在我俩对话的瞬间,女作家郭苏华轻盈地闪到他另一侧——原本属于两个人的画面,成了三个人的合影。当时心里掠过一丝淡淡的遗憾,仿佛独享的喜悦被瓜分去了一半。
我一直喜欢合影。因为影像让记忆不再单薄,它叠合了时空、人物与情绪,让某个瞬间变得立体丰饶。来南京报到那天,我就在微信工作群里提议:我们十七个人一定要合张影。很快便得到了响应,会议间隙,这个心愿圆满达成。


我还与“新大众文艺”代表人物王计兵、常玫瑰等作家留下了合影。常玫瑰与王玉兰总是形影不离,那天我与几位徐州作家同常玫瑰拍完后,再寻玉兰,她却悄悄退隐了一旁。直到她回家后发来信息:“有我俩的合影吗?”我怔了怔,回翻手机里的相册,无所有获。她的询问,放大了我的一份淡淡的怅惘——这场盛会中,还有那么多想合影的人,因为机缘、时间,终究未能并肩同框入镜。说真的,我甚至想过和每一位代表都留一张合影,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所幸,那张四百多人的大合影,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也放大了这场相遇的欢欣。临别前,我看到江苏文学院作家班的同学陆丽华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南京眼”的照片,心神一动,便也赶到江边。我想让这次金陵之行的喜悦被这双“眼睛”看见,也想好好看看它——心里浮起的,是那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请一位开着清扫车的师傅帮我与“南京眼”合影。回盐城的车上翻看照片,发现师傅把我拍得有些偏、有些小,“南京眼”却是清晰而宏阔的。我没有懊恼,反而轻轻笑了出来,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在《青春》杂志上读过的一首诗,叫《拍照》,依稀记得有这样几句:
“我整理衣帽/依偎华表/摄影师正忙着为我拍照/我要拍下天安门的全景/哪怕把我拍得很小,很小……”
是呵,留影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于人在画面中央占得多满、多显。有时候,我们甘愿成为风景里一个轻盈的注脚——因了这一刻,因了文学的盛会,我们欣然走进了风景之中,共襄美好。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