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第十四届江苏书展“新华书房”读书分享会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一年一度的“书香盛宴”拉开序幕。这是一场既安静又丰盛,充满内在律动与生命共鸣的精彩分享——围绕“让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著名“外卖诗人”王计兵、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山海情》编剧杨筱艳、坚持在地书写的宜兴作家乐心共聚一堂,以“非职业写作者”的独特身份,讲述文学与人生相遇所碰撞出的无限可能。
活动吸引了上百名读者自发参与,有读者从南京、宁波、上海等地赶来,现场年纪最大的读者91岁,最小的9岁,活动结束后读者们仍簇拥着作家热烈交流,久久不愿离去。这一幕令人动容的书香风景,呈现了文学的另一种质态和面貌:文学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文学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文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文学的“种子”落在心里
谈到与文学的结缘,1969年出生的王计兵回想起年轻时那段灰暗辛劳的打工岁月。1988年,王计兵初中都没有上完,就跟着建筑队出去做了农民工,踏进工地的第一天,他对人生怀有的美好梦想就被现实击了个粉碎。

每天,工长倒给他一袋钉子,让他把一根根弯钉敲直,这样敲上一天,工资是3块5毛钱。怀揣着对未来的迷茫困惑,他开始用跑步打发漫漫长夜,每晚都要跑上10公里,直到有一天,他在路边昏暗的灯光下与旧书摊相遇。面对亲切的文字,他想起课堂上学过的都德《最后一课》,生出了“久别重逢”之感。他和老板商量:让我免费看书,就当给你做个伴。老板应允,条件是不能影响卖书。于是每天夜幕降临后,王计兵就来到旧书摊,在昏黄灯光下如饥似渴地捧读古龙、金庸、琼瑶……每次还没看完,书就被读者买走了。遗憾失望之际,他想到高鹗续写《红楼梦》的故事,开始给那些有头无尾的故事“安排”结局。直到1992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
“爱好是有惯性的,你喜欢它的时间越久就越舍不得放下,自从有了文学,我不再感到迷茫,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王计兵说。

对杨筱艳而言,与文学的结缘得益于良师益友。小学三年级时,她被老师“抓包”参加区里的作文比赛,“不小心”得了一等奖,获赠《少年文艺》杂志等青少年读物,其中一本《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集》犹如神奇魔盒,打开了她与文学的奇妙机缘。
“谁是莎士比亚,谁是狄更斯,谁是哈代,谁是雨果、鲁迅、老舍……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有了一点点朦胧的理想。后来我又在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奖,语文老师单炎钊用他半个月的伙食费,给我买了一本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唐宋词选》。”
因着文学的感召,上大学时杨筱艳开始创作投稿,屡屡失败,她的大学语文老师严肃地对她说:“筱艳,你搞错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顺序。你还没有读书就要写书,你还没有生活你就要写作。”老师的话犹如一记重锤,此后20年间,杨筱艳不再“闭门造车”,而是专心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直到38岁时她接手了一个棘手难管的班级,成为她“非写不可”的机缘。
“这个班级的孩子特别调皮捣蛋,我想到用教育叙事的方式,在博客上更新自己和孩子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来解决教学中的困惑。等我贴到第23章的时候,有一位编辑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出书,于是就有了我的儿童文学处女作《五四班那些事》。”杨筱艳说。学校的良师,书籍的益友,生活中那群可爱可气的“小破孩”们,因缘际会地指引她步入了文学的殿堂。

宜兴作家乐心出生在太湖边的周铁镇,她形容自己与文学的缘分就像一颗种子被风吹拂,“自然而然地落在心里”。
小时候,爸爸妈妈上班以后,乐心就站在门槛上看来来往往的人,她看农民上街,看街坊邻居交谈,看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就像罗大佑歌里唱的那样:为什么太阳总是下在山的那一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这种对生活的幻想和好奇其实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乐心说,“我20几岁考上宜兴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从此接触到广阔的世界;我成为副总编以后,开始不满足于一事一议的通讯报道,想用文学的语言来反映世界的温情、世间的甘苦,传递人与人之间柔软的东西。写了散文还觉得还不够,于是有了更大体量的长篇小说《十八拍》。”乐心告诉读者,写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她可以“借千万人的眼,感受千万种人生”,自由地安排人物的命运,让现实生活中没能在一起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她也在文学中谈了一场又一场丰盈的恋爱。
在平凡生活中追寻生命之光
2021年的热播剧《乔家的儿女》让观众熟知了杨筱艳的B面——“编剧未夕”,随后,她又参与集体创作电视剧《山海情》。文学如何扎根大地、获取养料,同时超越生活、成就荧屏经典?读者渴望了解“编剧未夕”点石成金的密码。
谈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杨筱艳忆起母亲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堪称文学版的“孟母三迁”:小时候,杨筱艳的父亲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分配到一套郊区住房,母亲却用这套大户型置换了鸡鸣寺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被家里人嘲笑她傻。但是多年以后当杨筱艳创作《乔家的儿女》时,童年的那些烟火记忆竟奇迹般地扑面涌来:不负责任的“乔祖望”,温柔善良却命运多舛的“乔三丽”,街坊邻居捧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张家短李家长……一个个人物争先恐后地钻到作者的笔下,在二维的纸面上变得鲜活、立体和饱满。杨筱艳以女性作家的温柔悲悯之力,改写了记忆中那些被戕害摧折乃至凋零的命运。
《山海情》则是杨筱艳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乡村题材。忆起现实生活中70多岁的“水花”原型,杨筱艳感叹人物身上蕴藉的生命能量以及生活本身具有的力量:包办婚姻,丈夫瘫痪,为了养家糊口,“水花”每天凌晨4点起来做面条,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有一天她实在太疲惫了,竟在车上睡着,一下子把车骑到麦田里,一早晨做的面条全部被打翻,她绝望地趴在地上哭了起来……“然后她怎么办呢?她哭了一会儿坐起来,坐在田埂上,看太阳渐渐升起,照在金黄的麦穗上。她把眼泪一擦,重新扶起车子继续往前。那种坚韧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忘记技巧,忘记文学的手法,只想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作品离不开生活!我又一次深切地理解了老师对我的教导。”

这种属于“人”的力量,也体现在乐心笔下那些活泼泼的乡土生命里。乐心称她的新书《樱红蕉绿》是一本“时间之书”,一本“生命意义之书”:“我在乡土大地上追寻,那些皓月之光、那些萤火微柔之光,都是大地上的生命之光。”
乐心说,她笔下的人物有的是像赵亚夫这样的“皓月之光”,但更多的是那些平凡的生命,他们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而是“一把种子落在泥土里开出花来”。“我曾在沙塘港村碰到两个老头老戴和老裴,77岁,想亲自打一艘扯篷船,把太湖地区的风情符号和乡愁记忆留存下来。村里人都说两个老头发痴,老戴反驳:我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他们打船一年,我跟踪了6个月。2021年6月23日,这天太湖的风力正好,我们坐着亲手打造的扯篷船荡漾太湖之上,在船上大声唱道: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还看今朝……”
乐心说,那些闪耀着生命荣光的小人物,让她想到蒋捷的一句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过去我读这首词的时候总是想,人活着活着就没了;而当我与那些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人相识相遇的时候,我真正体会到,流光没有把我们抛弃,我们生命的精神就凝结在蓬勃的绿芭蕉、甘美的红樱桃里。”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这是王计兵最新诗集《低处飞行》中的同名诗歌。
王计兵告诉读者,送外卖时踏上的崭新道路常给他带来创作的灵感。书展期间,他坚持骑电瓶车往返于昆山家中和苏州会场,当他拐到小路时,诗神如约而至,他打开手机用语音创作:我仿佛是装进容器时飞溅出来的一滴水/而我扶住电瓶车的车把,只要我用力/我的双臂就会笔直,像一个“=”/而我弯曲的双腿恰恰像“《》”/我愿意用这个“《》”,括住我一生的水滴……
王计兵说,目前,全国拥有超8400万名快递员、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其中仅外卖小哥就有1300多万。庞大的“小哥”群体促使他更多地思考小哥的“明天”、呼唤小哥的“春天”。通过对身边的外卖小哥进行问卷调查,他得以倾听许多同行的故事。《低处飞行》中有一首《八根肋骨》,写一位同行在雨天送餐时摔断了八根肋骨,这个故事让王计兵感到“特别痛苦”。“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他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他本身个子很小,摔断肋骨又减去两厘米身高,写的时候我特意提到一个细节,说他老婆从前就比他高,现在比他更高了。”
王计兵还认识了一位曾获“五一劳动奖章”的女性外卖员,他觉得奇怪:一个文文弱弱的女子,怎么那么喜欢爆粗口骂人?走近了之后他才发现,是女性外卖员面对世界时内心深处的强烈不安全感,才让她选择了一种错误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她实际上是用粗鄙的语言,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看似坚硬的外壳”。
有了文学我们才是生活着
从报社副总编的位置退休后,乐心说她“像一条鱼塘里的鱼奔向了大海的宽广”,这片大海就是她的故乡。一个见多识广的媒体人,为何退回到故乡这片“狭窄”的天地?在生命的原点,她与文学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动人故事?
“媒体人的特点是天天跟世界对话,唯独没有时间跟自己对话,所以回到故乡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大地上的一棵庄稼。”乐心动情地说。
退休后,乐心在家乡认识了一个90岁的写碑人,他年轻时毕业于无锡师范,后因生活变故依靠写碑为生,家乡方圆20里内的桥碑墓碑都是他写的。“他说,丫头,人在这个世上就算落到最低处,我们都要能站起来,要有一点本事。当他喊我丫头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了,因为我的双亲早已去世,再没有人叫我丫头了。文化站站长看到我掉泪对我说: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感动、不能掉泪,她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感人。”
回不去的乡村,挥不去的乡愁,乐心的“返归乡土”不是退居一隅,而是以故乡为场域、以“庄稼”为视点,观照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再生的时代图景。而在今年7月,作家杨筱艳也正式退休,告别了自己坚守数十载的三尺讲台,她在“8小时之外”追寻文学理想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读者。

没有朋友圈,不刷抖音、小红书,婚假只休1天,产假没结束就上台赛课……“工作与创作如何平衡,我抓住一个原则:在学校绝不做私人的事情,在家绝不做工作上的事情。晚上回到家,雷打不动,每晚写上三千字;在学校,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上课、改作业、做PPT、出卷子、课后辅导、看护学生吃饭做操,全情投入在学生身上。”
她和学生之间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一位当年很优秀的女学生告别痛楚的婚姻后,和女儿站在向日葵花海里,合拍了一张寓意“新生”的照片送给了杨筱艳。在她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期末考试后,一名“差生”史无前例地取得了英语89分的优异成绩,他送给杨筱艳一张贺卡作为离别礼物。其中除了附赠自己的照片,还有自己攒下的20块钱,他用他童稚却饱含真诚的方式,向亲爱的“杨老师”献上一份感恩和敬意。
“55岁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算不算铁树开花……”这是王计兵诗集《低处飞行》中的一句,写尽了文学带给诗人的苦涩与甜蜜。“铁树开花”背后,是王计兵因为家人的激烈反对,长达25年的只创作不投稿的幽暗时光。
为了体验小说人物失去双亲的悲痛,王计兵身披白布模拟披麻戴孝,结果被街坊误会,他父亲气得大发雷霆。于是有一天,王计兵结束白天的捞沙工作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婚后,由于王计兵的爱人也不喜欢他写作,为遵守自己对家人的承诺和责任,他在长达25年中没有投稿,却无法“戒断”阅读和写作——在拾荒得来的废纸上写诗,捡到书后读完再拿去卖,实在没书读太难受了,就去新华书店买本新书,然后放在泥土里“做旧”,再大大方方地拿回家……
“直到2019年我在网络上发酵后,才和爱人坦承自己在写作,可我爱人却说她早就知道了,原来她洗衣服时经常从我口袋里掏出圆珠笔、钢笔,都扎坏了几件衣服——原来我们家演了一出‘谍中谍’啊,还演了那么多年。”王计兵的话语里,透露着被“宠溺”的羞涩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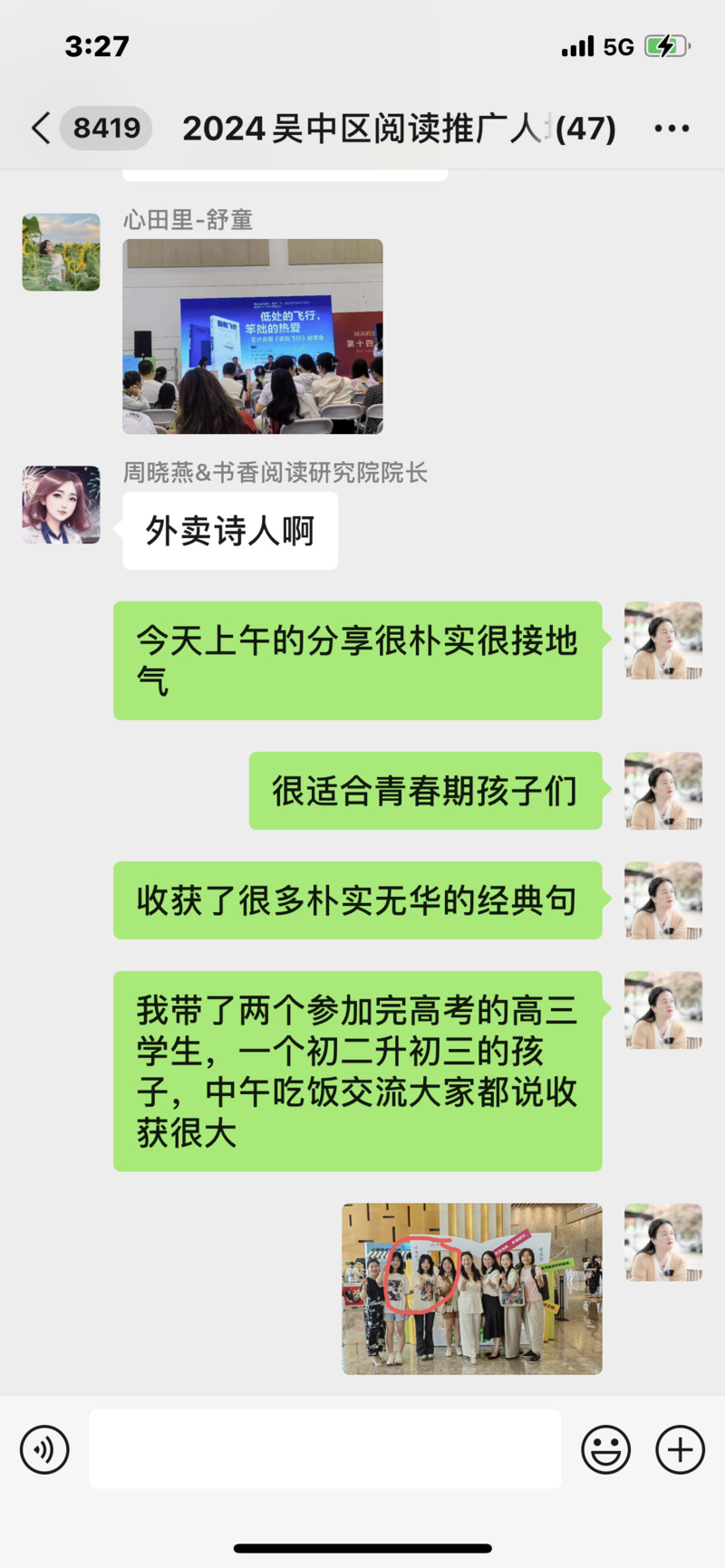
这些文学故事夹杂着生活的体温,浸透了人生的苦涩与温柔,深深打动了线上线下的读者们。作为“斜杠作家”,几位嘉宾均不以文学为生,这个“生”,是“生活”;他们又以文学为生,这个“生”,是生命。对他们而言,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他们如此坚守?
“等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有人指着我的墓碑说,‘这个人喜欢文学,用尽了一生的时光’,可能是对我最大的褒奖。”王计兵说,“我认为文学可以修正一个人,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好人,我更相信文字是所有事物的种子,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字、喜欢文学,只要我们拥有了种子,春天迟早会来。”
“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需要一道光,对我来说这个光就是文学。电影《死亡诗社》中的教师约翰·基丁是我的职业明灯,他跟他的学生说过一句话:‘对的,法律、建筑、经济,所有这一切是构成我们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文学、艺术、诗歌、美,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对我来说,文学很简单,就像洗脸刷牙一样自然;文学又很崇高,没有文学,我只是生着、活着,有了文学我才是生活着。”杨筱艳说。
在乐心看来,文学让人类在平凡世界里葆有一颗勇敢的心,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文学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河流之上的一座桥,人心与人心之间相互连接的心桥,让我们体会生命的饱满。乐心说,她在今天的分享会现场看到了很多从外地赶来、为文学奔赴的读者,这种书卷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岁月“包浆”,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光泽,拥有被文学打磨的温厚“包浆”。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于锋/文 余萍 赵亚玲/摄 华苏杰 赵宇/视频







 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














 Android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iPhone版




